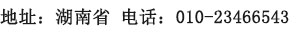文/图:脑袋周
年10月于北京
边检的人说我是第一个从中国到澳洲的workingholidayvisa的持有者,这话不知真假,但我确实是出签的那一天就立刻订了机票。带着爸妈“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嘱托”,和大学时攒下的所有积蓄出发了,一路忐忑而期待。
初到澳洲才明白这里的人们对咖啡质量的要求很高,略懂皮毛的我,做咖啡的手艺也确实跟不上那颗只想安安静静站在咖啡机后面的心。所以找工作的范围也不得不从barista扩展到了整个hospitality和sales,找工作的方式也从在Gumtree上投简历变成了拿着简历挨家挨户自我推销。
我记得那天抱着简历从王健林“爸爸”的Hoyts电影院出来时,正好看见门口一家咖啡店的中国老板在收店,虽然中国老板压榨员工的海外形象深入人心,但是迫于生计的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顺手递上一份简历。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顾虑至少在这家店是多此一举了。
上班第一天得知老板是人大99级的师姐,首席咖啡师Alvin是在新西兰咖啡师大赛里拿过不俗成绩的masterbarista,于是我就老老实实从floorstaff做起,端咖啡、送简餐、刷盘子、扔垃圾、搬牛奶、学做冷饮、一脸懵逼的用系统点单……反正一切跟咖啡师不沾边的活,我基本都干了一遍。一天7、8个小时只有午餐的半个小时能坐着,但也没觉得多累,天天还傻乐,推着trolley倒个垃圾还能跟购物中心的保洁大哥聊上几句。没过多久,大概Alvin看出了我隐藏的慧根,开始亲自指点我做咖啡。
澳大利亚是一个星巴克生存不下去的国家,辽阔的国土上只有二十二家星巴克集中分布在大城市里。走进任意一家,你会发现一半以上的客人都是亚洲人,而一半以上的订单都跟咖啡没有关系。大概可以不负责任地得出结论,一杯品质上乘的咖啡跟星巴克基本没什么关系。这里不是在说星巴克没有好的咖啡师,只是全球标准化的咖啡豆烘培、配送以及对所有门店口味一致的追求,使其在独立咖啡店遍地的咖啡消费大国难以立足。
我所在的堪培拉虽然不像墨尔本那样被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