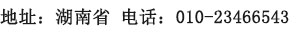夜幕下的拉巴斯静谧而空荡,渐入深冬,太阳一落山,冷风四起,没有人愿意出门。远处的大雪山积雪更厚了一点,头一天凌晨的一场大雪让这座城市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地通通银装素裹。山上点点连成排的灯光点缀着没有星星的天空。这些灯不过是贫民区的简陋的照明设施,白天黯淡,小孩子把两边灯杆当作球门,没有车的时候,马路就是足球场。夜晚华灯初上,贫穷,简陋,灰尘,黄沙在黑夜里不见身影,从远处看,贫民区变成了灯火灿烂的山城。这景象,有时候还变成了城市名片被印在明信片上。
南区是个幸运的地方,大雪不会下到这里,寒冷也不见太大威力。奇怪的是,高原的人似乎更怕冷,他们有着敏感的气温神经,气温降一度,身边就会有人讲——哎!今天更冷了!气温降两度,每个人就开始加衣服。降五度,健身房的人明显减少。彼时的街道街角没有飘来烤牛心的味道,看来那个以为年年如一日的卖烤牛心的老妇人也回家取暖去了。我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冷风从衣领口钻进身体,不由地颤了一下。一年了,快一年了。这座四周环山,鲜有绿色的城市。这座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的城市。我是如何生活了一年的呢,我不禁问自己。也许就是靠着当初来到这里决定不再回头的勇气,也许能够贴近南美大陆带来的血液里的某种积极因子,也许终于敢独自面对孤独。倘若今日我忘记带家的钥匙,这四下无人的街,我竟不知道可以打电话给谁。想到这,我伸手摸了摸包里的钥匙,还好它安然无恙。十二街是不管去哪里都要途径的路,右转通向城中心,左转是回家。路口有三个街头艺人,平日里,他们混迹各个区域,在红灯时候,就在路口玩耍一些小玩意儿,然后向车主要取赏赐。今晚可能太冷,他们把杂耍的工具换成了火把。我来来往往很多路口,红灯时候都在匆忙过马路,不曾欣赏过任何一个表演。‘嗨,你还好吗?’其中一个梳着脏辫的街头人士跟我打招呼。我想我大概是想着什么东西让别人看出我出神的样子。也是,这样寒冷的夜晚,怎会有人有兴致看无聊的表演呢。‘嗨,我没事,只是想起来还没看过街头表演。我希望我的回答不会觉得奇怪。’‘这么说来有点,哈哈,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在乎。’脏辫摇着手里的火把,露出略带疲倦的欣慰的笑容。‘这么冷的天,不找个地方休息吗?’‘对我来说不算冷,虽然已经下雪啦。看,我就穿一件衣服。’脏辫说完晃动起身子。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再说我也没有家呀。’‘哦,你是哪里人?’‘墨西哥。’‘很有意思,我马上就会去那里旅行。’说来也奇怪,不知从何时起墨西哥就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符号,一个即遥远又亲切的符号。我到了很多南美地方旅行,马上结束一年的征程,选择墨西哥作为一个完美的结尾显得意义非凡。‘真的吗,你会爱上那里。’脏辫似乎也挺高兴的。‘既然喜欢,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我和你一样喜欢旅行,只是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就会上街做一些表演。说实话,这也蛮有趣的。’火把闪耀着火花,映在一张沧桑的又有那种内在精神的脸上。‘你都去了哪里旅行?’‘我辞掉工作以后——虽然我的工作跟屎一样,辞不辞也无所谓啦。从墨西哥城出发,去往墨西哥南部。然后去危地马拉,那个鬼地方没什么可待的,我本想找一点零工做,处处碰壁,工资很低。接着去哥斯达黎加,那真是个好地方,那里有个小岛,岛上的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没有工作没有钱,有个老师在那里教授巴西战舞,不收钱,那地方很热,我们住在岛上,随便住个帐篷,有时候直接睡在沙滩上。我在那儿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后来去哥伦比亚,说真的,这里跟波哥大挺像的。那时候我没有钱了,我想继续再学习巴西战舞,就去了巴西。我在里约在了一段时间,开始在街头做一些工作赚点钱,主要是编脏辫,然后再跟别人一起练习战舞。里约街头艺人可太多啦,水平都很高。再后来就来了玻利维亚。’他滔滔不绝地梳理起这段经历,好像有段时间没有人这样问过他了。‘听上去你已经花了好些时间在路上了。’‘对,我已经离开墨西哥城2年多了。’‘还要去别的地方吗?’依照我对这种旅行方式的了解,大多数人都会绕南美洲一个圈。就像在亚洲也有青年人会花一年两年在东南亚绕个圈一样。‘不知道,这里太冷了,本以为我不会在这里太久,但是我在这里找到了组织。’‘组织?街头艺人组织?’‘忘了跟你介绍,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这时对面街口过来两个人,一个手里拿着火把,另外一个踩着独轮车。‘他们一个是巴西人,一个是乌拉圭人,我们都是在组织里认识的。’‘在上面那个区有两个乌拉圭人做手工艺品,我买过他们做的耳环。’南美洲国家因为经济崩溃,失业人数剧增,年轻人很多失业在家,没事儿可做,就开始长时间的旅行,越到后面越穷,很多人都会做点小东西或者上街表演。这里面以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人最多。除了失业以外,我觉得在南美洲盛行这样的方式也跟他们是个浪漫的地方有关系。有的人效仿切格瓦拉穿越拉丁美洲,他们骑摩托车,竖一把红色的旗帜,来象征革命。‘我认识他们。’脏辫回头跟乌拉圭白人小伙笑了一下。‘在市中心往上不到阿尔多的地方,有个老房子,里面有人画画,有人写音乐,有人写作,我们就住在那里。’这应该就是他说的组织。我在心里想。‘你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嬉皮士的地方?’我问。‘没想到你那么快就理解了!’脏辫很惊喜,大概是因为有人会用嬉皮士来形容他们。‘你们在那里干什么呢?’‘有很多事可做,当然你也可以说没什么事,那里不需要付钱,我们上街表演只要钱能够买点吃的就能够维持生活。’骑独轮车的巴西人过来,递给脏辫一包牛奶。‘世界上总是有人这样超然物外啊。’我感叹道。‘哈哈哈,也许吧,生活的方式多种多样,刚好在你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负担的时候可以超然物外。’他们三个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快走了,也许有时间我们再在这个路口聊天吧。’‘当然,最近我们都在这个区。星期六下午怎么样,我们会来这里表演。’‘这个不确定,但是如果你们在,总会遇到的。’‘虽然我想介绍你去参观那座嬉皮士房子,不过里面太不堪了,又脏又乱,也有神经病。’乌拉圭小伙说道。‘这样的话,我想还是在这里比较好。’我跟他们道别,准备过马路,骑独轮车的巴西人戴上一顶尖尖的小丑的帽子,在鼻子上按上红色的夸张的小丑鼻子,格外开心的说,‘我陪你过马路。’一进家门,一阵凉风迎接了我,原来是窗户没有关紧。家里的温度居然跟室外一样冷。月光暗淡,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张两人坐沙发和一张圆桌。我有多久没有坐过这张沙发了?两个月?三个月?这张圆餐桌只是用来堆放回家整理的文件和笔记本电脑。墙角的百合花已经变成了枯萎的丑陋的干花,连杆都变黄了,还记得买来的时候美丽动人的模样。肚子有点饿,在这种又冷又孤独的时刻,食物还算能抚慰人心。打开冰箱门,里面静静地放着一排酸奶和四瓶罐装可乐,别无他物,都是那么冷的东西,没法吃啊。我的遗憾又深了一截。并不是每一晚的月光都皎洁动人,并不是每一场大雪都凄美浪漫。那么梦里呢,我躺在床上想。
山茶花Janiceanice欢迎投稿给这邮箱yxybjad.北京有专治白癜风的医院卡泊三醇价格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