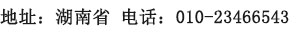安娜私下是个低调安静的人,她留着一头黑色卷发,喜欢穿一身黑色,别人说话时总是认真倾听,偶尔插几句话,或者点点头表示赞同。如果不是左脸颧骨上的乌青和左手上缠的绷带,很难猜出她的职业。
搏斗场上,安娜的艺名是“复仇者安娜”,在那里她换上紧身亮皮衣和点缀着金属闪片的皮靴,露出壮实的肌肉,在干冰形成的雾气和高频率闪烁的红色灯光中吼叫着跑上格斗台,跳上拦住台子的绳索,挥动双臂调动观众的欢呼。
这是疫情后埃尔阿尔托市赛哈体育馆第二次举办自由摔跤表演。位于高原盆地的拉巴斯无法承受迅速增长的人口后,西部的卫星城埃尔阿尔托开始发展起来。“埃尔阿尔托”在西语中意为“高处”,海拔多米,虽然我基本没有高反,但让一个米四分半都跑不进的人在这里走一天实在是一种折磨。高原城市的人口分布是残酷的:有钱人住在海拔最低的山谷中,住房海拔随着收入的降低不断增高,最贫穷的人则被挤到比拉巴斯高多米的埃尔阿尔托。这儿的主干道总是挤满动弹不得的车辆,每逢集市更是人头攒动,坐在缆车上也望不到下方摆摊的橙色帐篷队列的尽头,每次进去我都得隔10分钟问一次路。赛哈体育馆就位于集市最热闹、人流量最多的区域。在本就热闹的市场里,体育馆门口的大喇叭以极高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门口支起一张大海报,上面都是自由格斗的参加者,他们带着各色头套,露出凶狠的眼神,双臂交叉展示着肌肉,下方写着每个人的艺名:
吸血鬼吸血鬼二号
复仇之影
萨巴拉上校
玻利维亚最后的王者
9号罪犯
不死者
破坏者
食人鱼
拉美自由格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玻利维亚的自由格斗在90年代初开始盛行,直到现在仍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运动。我买了一张票,在体育馆门口排起长队。为了营造表演氛围,3点的演出拖到了4点半,工作人员搭建起一个3米高的台子,两台机器喷射出浓重的雾气,场上投射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每轮格斗前,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两名裁判跳着滑稽的舞步爬上摔跤场,接着主持人用拉美足球解说员特有的压抑语调和拖长语速喊出每位格斗者的艺名:“准备好了吗?接下来上场的人你们期待已久,上周被打败后她发誓要复仇!她就是———复仇者———安娜——————”。安娜拉开帘子来了个闪亮登场,接着她绕观众席挥动着双手巡场一圈,男女老少开始欢呼吹口哨。场下安娜解释道,拉美的自由格斗是“7分打斗,3分表演”,格斗技巧和戏剧性同样重要,一个优秀的格斗手也是优秀的戏剧演员,懂得如何调动观众气氛。
安娜成功调动了坐在我前面的一家8口人的情绪,这一家子都是这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场场不落。他们最喜欢的格斗手是“破坏者”和“食人鱼”,5、6岁的小朋友戴着破坏者半边蓝色半边金色的周边面罩,站在座位上蹦蹦跳跳。他的爸爸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嚼着炸猪皮的嘴随着每次摔落发出激动的怒吼声。“复仇者安娜”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她巡场跑过我们这一区时,一家人伸出大拇指向下,发出一阵嘘声。她的”对手“凯蒂穿着土著传统服装,在印第安音乐的欢快笛声中转着圈亮相,观众席一阵欢呼,显然她是“正面角色”。
主持人简单检查了两人的鞋底后,对决开始。两人隔着一米盯着对方,警惕地转着圈思考下一步动作。凯蒂先瞄准安娜的腋下冲了过去,安娜一个闪躲逃过一劫,接着迅速向对方的方向一仰,整个身体压在凯蒂身上,咚的一声,两人摔在地上。压了几秒钟后,安娜起身,将动弹不得的凯蒂推出格斗场外,凯蒂倒在vip观众席的地上。安娜顺势站到围绳上,向观众挥了挥手,然后在口哨声中跳了下去,重重压在凯蒂身上,凯蒂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我心里一紧,仿佛能看到在安娜壮实身体的重压下骨头折断的场景。戴着破坏者同款头套的小朋友比我淡定的多,边蹦哒边鼓起掌来。我的担心开始从凯蒂的安危转向小朋友的心理健康。
后来安娜说,这些动作其实都是设计好的,演出日前的一周,每对选手都会设计脚本,包括本场赢家输家、要做的动作及表演的内容,接着便是根据脚本不断练习彩排,摔是真的摔,疼是真的疼,不过专门的技巧练习能使他们最大程度上降低受伤的可能。
在安娜和凯蒂的本周剧本中,安娜先赢一局,凯蒂再扳回一局,接着安娜反击拿下最后一局,完成“复仇者安娜”的使命。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第二轮摔跤手们经常摔下赛场,在观众前直接厮打。这一轮安娜的力量明显弱了很多,凯蒂一个上勾拳,直接将她打飞起来,摔在地上的安娜摸着下巴想起身反击,不料凯蒂继续压在她身上,掌声越来越响,输了这一轮的安娜气急败坏,她发出一阵阵尖锐地吼声,朝着观众席破口大骂,接着拿起一位vip观众的可乐,大手一挥泼到对面观众身上,人群中传来一阵阵咒骂声。安娜嘴巴一撇,把瓶子一扔,跳上台挑战第三轮。第三轮依然按照剧本走向进行,胜利后的安娜不顾一片嘘声,掐着腰啐了一口,朝观众席破口大骂了几句,走回了后台。
下一场打斗中,几乎没人注意到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女人偷偷从后台走出来,我瞅了好久才反应过来,这是刚才威风凛凛的安娜。她一声不吭地拉了张凳子拖到vip席最后一排,继续看同伴的表演,10分钟前还在场上狂吼的安娜,现在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
华妮塔是一位“乔丽塔”,疫情前她也是自由格斗手。在玻利维亚,“乔丽塔”是对艾马拉和克丘亚族土著女性的称呼,她们具有鲜明的外貌和装扮特征:窄边高筒圆帽、两束乌黑的长辫子末端绑着一撮假发、内部由层层衬裙支撑起来而显得格外宽大的彩色裙子,因为背上巨大包袱的重量而弓着腰走在街上。当西班牙人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当地女性身着黑底彩色边的羊驼毛长袍,脖子上围着一圈或圆或方或模拟动物形状的装饰布料,腰间系着一条耷拉到膝盖的绳子。颇为不爽的西班牙人在年颁布了一条法令,禁止土著女性着传统服饰,改穿简单的衬裙,即西班牙的女仆的通常装扮,以使她们忘记自己所属的族群,永远依附于西班牙人。独立后,适应了这种装扮的土著女性逐渐将其作为民族和历史的象征,并以此为荣。“乔丽塔”(cholita)是“乔拉”(chola)的指小词,这个名称曾经带有贬低意味,她们在玻利维亚受到歧视和压迫,地位极低。如今乔丽塔们的地位已提高不少,但她们仍然在从事报酬最低、又苦又累的岗位。走在玻利维亚西部,乔丽塔随处可见,看到她们我总是想:为什么没有“乔力托”?土著男性去哪儿了?很多玻利维亚人也给不出答案,根据他们的猜测,也许土著男性的装扮没那么显眼,也许土著女性才是家庭的主心骨。
我跟华妮塔在拉巴斯市中心的市场见面时,她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黑色圆帽子。她解释道:
“我妈妈和丈夫最近因为新冠去世了。”我开始觉得这个时间与她约会见面是个错误,但她神情平静克制,让人看不出家人的去世对她的打击究竟有多大。
与大多数玻利维亚的自由格斗手一样,华妮塔的主业并不是格斗。她在埃尔阿尔托和拉巴斯各开了一家售卖印第安节日祭品的店,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玻利维亚做这行赚不了多少钱,何况一周只有一场,一个月下来也就挣块钱。去国外演出的话挣得倒是多一点,我去过美国和日本表演,收入都不错。格斗主要还是兴趣爱好,观众开心了,我们也满足。”
华妮塔今年39岁,看起来更年轻一点。由于曾受到歧视和不公待遇,许多乔丽塔沉默寡言,聊天时总是用戒备的眼神看着我,话则是能少说就少说。但华妮塔非常健谈开朗,甚至看不出她最近遭受了这么大的变故。她从小练习跆拳道,10岁时有位教练相中了正在练习的她,邀请她尝试一下自由格斗。当时正是这项运动在玻利维亚兴起之时: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答应了。它跟跆拳道不太一样,甚至拉美的格斗跟日本的也不一样,赢不是主要目的,你要取悦观众,要让格斗具备观赏性,观众开心,才是成功的表演。”华妮塔的艺名是“亲切的华妮塔”,我去看了看她的脸书页面,当时还年轻的她像平常一样穿着传统服装,站在赛场边向观众挥手。乔丽塔的参与是玻利维亚自由格斗的特色,华妮塔认为这是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比起戴上面罩就认不出人的男摔跤手,女性在场上大喊大叫、扭成一团的场面显然更为新奇,平常总是在街上弯着腰、略显笨拙的乔丽塔上阵更会引起观众好奇,组织者也有意招募一些乔丽塔,以此作为特色宣传。安娜和她的“对手”“乔丽塔凯蒂”的对决就是当天观众呼声最高的一场。
现在华妮塔有三个孩子要养,第一个儿子已经21岁,非常抗拒服兵役:“劝了他很多次,怎么说也要为以后上学工作着想,但他死活不愿意出去,现在还待在家里。”目前她还不想重拾自由格斗,一是疫情期间有所顾虑,二是妈妈和丈夫刚刚去世,没有心情和精力。另外8月份是印第安人祭奠“大地母亲”的时期,店里会非常忙。
“但总有一天我会返回格斗场,即使赚不到什么钱,毕竟我很喜欢格斗。”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